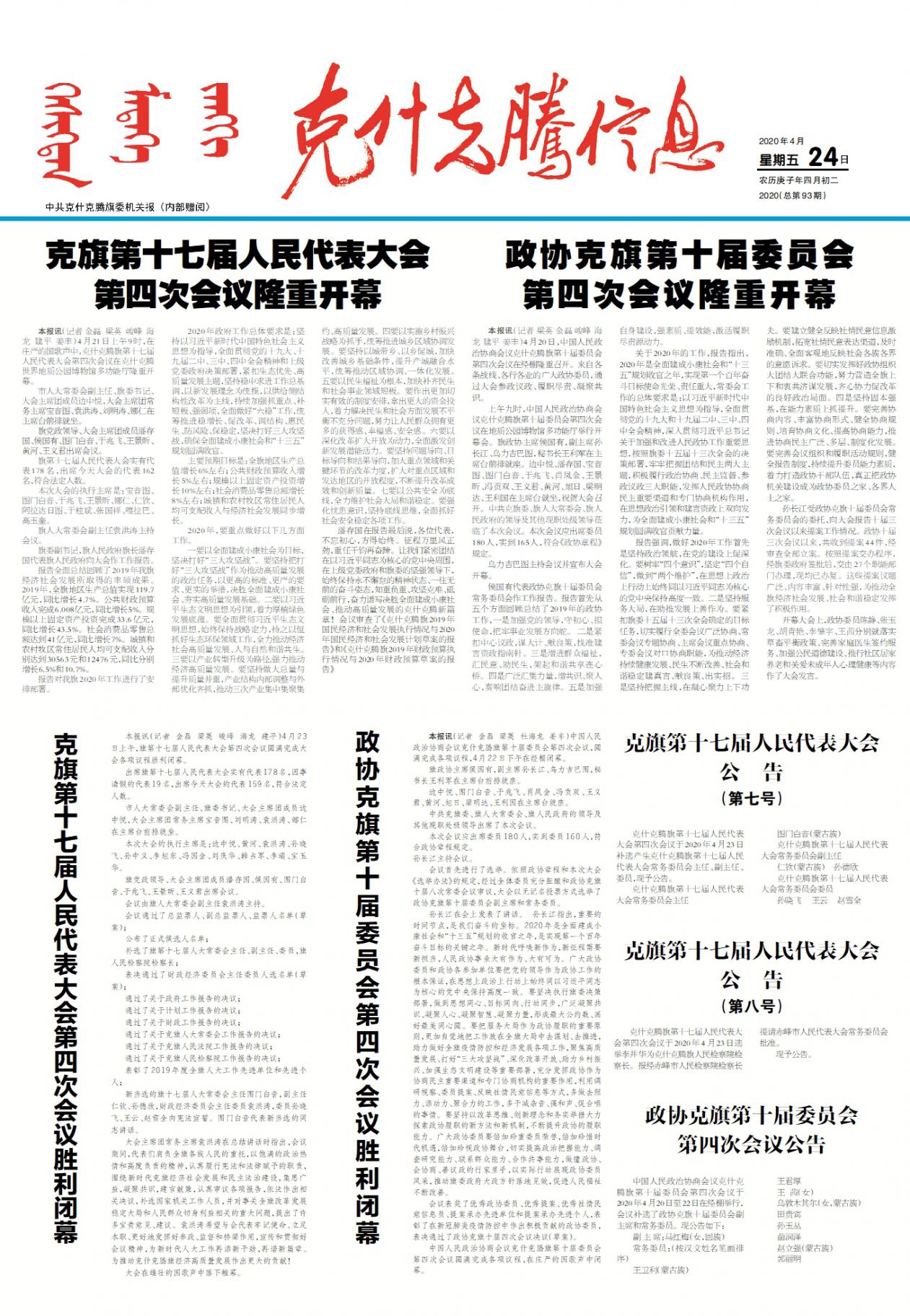第三版:3

二表哥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开镰的地头,找到一个足能隆起整个腰部的莜麦个子,咬咬牙、皱皱眉将身体铺上去,瞬间,如雷的鼾声震得身体下的莜麦铃铛瑟瑟发抖,丢在一旁的磨石、镰刀尽情享受这片刻的轻松与闲适。
三三两的割(读gā,音)地人也各找一莜麦个子或坐或倚,“哧哧”的磨镰声、风摇莜麦铃铛的“哗啦”声、旱烟袋的“吧嗒”声、二表哥打鼾的“呼哈”声声声交响。
这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小队秋日里经常上演的地头交响曲。
与种地、耪地、趟地来回算“一遭地”不同,割地要顺风或侧风向开镰,逆风向人们弯腰时麦穗会打在脸上。因此,割完一趟子地要原路返回割另一趟子。返回和磨镰的时间算一个“地头歇儿”。“地头歇儿”说白了就是走路、磨镰、抽袋烟的功夫儿(意为时间长短)。
大表哥是生产队的政治队长,因为割地速度快,始终占据“头镰”的位子,农业队长只好押后阵,这叫前边儿牵着,后边儿赶着,很符合政治引领发展生产的关系。中间落在后边的人被称“装口袋”。二表哥一米八几的身高,猫下腰屁股会高出地里的莜麦些许,是经常被装进口袋里的人。大家伙儿说,二表哥的腰硬,弯不下来。其实二表哥是村里叫得响的驯牛驯马手,再野性的牲口到了他手里都会变得服服帖帖,但他最怕割地。然而,农村的秋天,麦子要掉脑袋的时候,家家户户铁将军把门,除了卧床起不来的病秧子都要来割地。单项选择每每让二表哥犯怵。
人民公社时期以生产小队为单元的农事活动一般是用体力来划分的。男壮劳力驯牛马、赶车、扶犁、耪地、打草、扬场…讲技巧,而更多拼的是力气;女壮劳力倒粪、点种、薅草、割地、摊场、打掠…拼的是耐心,做的是灵巧;老小弱劳力身体力行就干一些放猪赶羊的杂事。
一般来说在庄稼又高又密的平川割地,女人们凭着韧劲、耐性干起“磨悠活儿”往往优于男劳力,但如果在视野开阔、庄稼稀矮的漫甸走马草原,女人的韧性就打了折扣,由此男人以天下为家,女人以家为天下管窥一斑。
“庄稼活不用学,人家咋着咱咋着”。年龄小时,第一次割地,就与队里一顶一的庄稼把式大表哥搭伴割一趟子地。一是学技巧,二是怕落在后面被装口袋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,正是我读初中的时候,春秋两季儿农村的机关和学校都要放七天左右的农忙假,学生除了寒暑假就多了十几天的假期,因此,四季农事对每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并不陌生。我最向往的事儿就是在一眼看不到头的漫甸上割莜麦。这样矮小的身材就有了优势。
我们住的村子在百岔川分岔的最上头,俗称把沟脑儿,坡大平地少,而前山后梁上面却是一望无际的漫甸草原,生产队就在上面开荒种地,俗称新荒地。刚开垦出来的地是“生地板儿”,未被驯服的两三年内只能种莜麦,待收复野性变成“熟地板儿”,才种小麦、土豆、青贮等作物。
割地腰疼是所有人的通病,高高瘦瘦的大表哥在实践中慢慢总结出了蹲马步的功夫,难题迎刃而解。他挺直腰板、抬头向前,蹲下的马步却在行垄间优雅从容,一副大步流星奔小康的姿态;他压低镰把,镰刀贴紧地皮平拉平移,一把儿把儿莜麦割下来,留下了齐齐整整的麦茬。他是第一个到达地头的人,回来时总要顺道帮落在最后的割根垄。
或许是为了减缓劳动者的心理压力,当地割地有个习惯,整块麦田一分为二从中间向两边割。大表哥辗转腾挪,不一会儿整块麦田已打开一个豁口,为人们铺展出一片劳作的空间。远远望去,心情豁然开朗。看大表哥割地,会淡漠劳累,是田垄间美美的享受。
七垄为一趟子地大多两人协作完成。出腰子很关键,读yào音。出完腰子,成片的庄稼就显得通透起来,心里敞亮,割地的速度就加快了。腰子相当于人的腰带,打腰子是用两把儿庄稼对齐分开,抓住穗头拧上两三个劲儿背上疙瘩,庄稼压在上边。捆时拧两个半劲儿,谓之捆腰子或捆庄稼。前者割三根垄,一根垄出腰儿打腰儿,再盘两根垄掏余下四根垄的腰口,这样就能与后者割的垄数相抵;后者盘四根垄,捆腰子。(盘、掏与割意相同)。
大表哥的走马腰子堪称割地一绝。一般人的做法是一根垄割到一定的距离,薅两把儿莜麦直起身在鞋上磕掉根上的土,拧成腰子后把割下的莜麦放上去,掏好腰口后前行。大表哥则不同,用最后割下的一把莜麦用小拇指隔开,与长着的莜麦拧成腰子,顺势将庄稼放上去。这是眼力活儿,眼到手到,隔出的一小把儿莜麦要与长着的莜麦相一致,捆庄稼时才不致于勒断腰子。减少了猫腰起身的次数,割地效率倍增。大表哥有一双蒲扇大的手,一般人抓六七把儿庄稼,两三米放一个庄稼个子,他抓八九把儿,四五米放一个庄稼个子,这给手小盘垄的我带来难题,割几把儿莜麦就得去送把儿,矮庄稼腰子不够长,捆时还要接腰子,经常弄得手忙脚乱跟不上趟儿。后来,大表哥把走马腰子的技巧传授给我,兄弟俩就成了黄金搭档,无人能敌。一次,三舅心服口不服,较劲与我比试,一袋烟的功夫,让我落了半趟子地。三舅悄儿没声地瞅我一眼,因为我没有掏后边四根垄的腰口。好在各干各的活儿,而活计自然留给了捆腰子的大表哥,留给大表哥的还有顺把儿溜出的莜麦,他会一一捡拾,不丢弃一穗粮食。
走马腰子是漫甸地、矮庄稼的专利,在川平地、水浇地的高庄稼处无法施展,只能平推慢行。
俗话说“麦子伤镰吃白面”,这是人工割地的讲究。一片麦田八成熟是最佳收割期,因为庄稼割倒后,秸秆里的水分养分仍继续供给麦穗。如果等到九成熟收割,割地、玛地、运输过程会掉粒儿糟蹋到口的粮食,等到十成熟儿再割,粮食粒大多掉在地里。另外,碾子磨熟透的麦子,磨出的全麸面发黑,面筋打了折扣,口感也不好。
如今联合收割机一次性脱粒,减少了割地、码地(把庄稼个子垛攒一起)、拉地(运庄稼)、垛垛、拆垛、摊场、打场、扬场等多个环节,然而人们几千年来敬畏土地、躬身刨食的一幅幅场景却永远镌刻在农耕的历史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