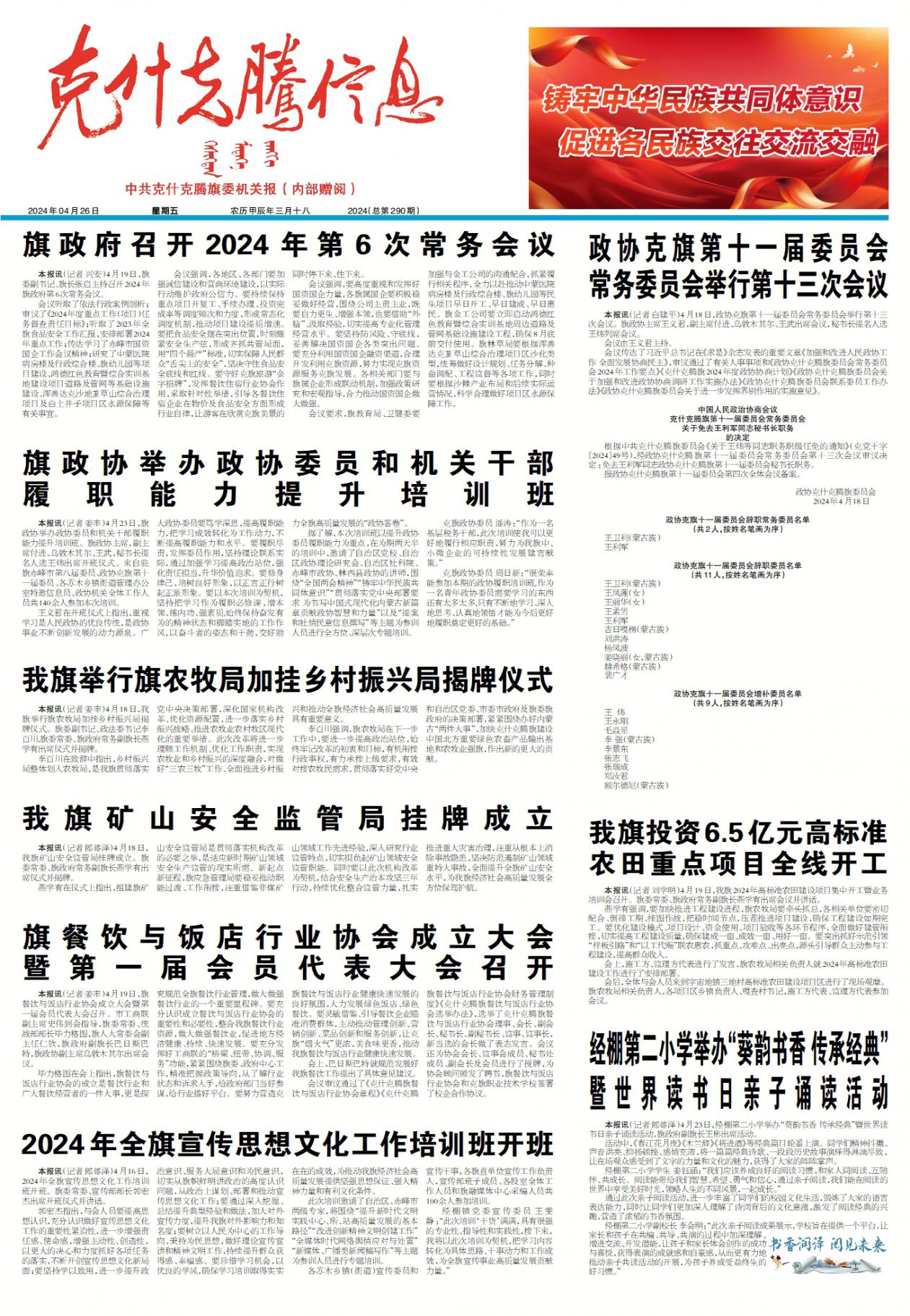第三版:3

摄影 张今卓
在北京这样一些大城市,一说到春天,人们总是想到梅花,而在北方,杏花承担着报春的任务。在经棚到万合永和土城子的路上,会经过一座座山,一座座山上绽放着如云朵一样的杏花,这些山上的杏花也是克什克腾春季的一道景观。
我出生的村子是一个叫裕泉隆的村庄。称裕泉隆就是因为有个泉子。全村人就靠这个泉水活着,山脚群石环抱,泉水如泓,像一个宝瓶日夜不停地流,人在上面吃泉内的水,马和羊喝泉子流出的水,下游的水给菜吃,它依着山坡蹦蹦跳跳,依次流进了张家的菜园、莫家的菜园、孙家的菜园。
裕泉隆依山傍水,这个村子没有小麦田,但不乏蔬菜香,家家都有碧绿的菜畦。人都说这裕泉隆的水养人,大姑娘特别水灵。大姑娘出嫁,把这里的水灵带出山沟,小媳妇嫁进来,喝上几年的泉水,也变水灵了。
我想,老祖宗从河北玉田一路向北出发,没有停留在承德这样的地方,经过林区和草原,但没有继续向北到通辽地区,一定是这眼清泉留住他们的心。
灰褐色的土,坚硬的砥石,给故乡带来活泛劲儿的是东山坡上的杏花。“东山坡的杏花开了”,这是裕泉隆人的第一句诗。抬头一望,一片粉云升起在东山坡上,孩子们和蜜蜂一起爬上山去,看着杏花的花蕾,凑上前去闻他苦苦的香味,这苦寒之地生长出来的娇嫩花朵,让人们看到了寂寞的生活里终究有甜蜜。
杏花的模样给了村人最初的艺术启迪。母亲给姐姐绣的花鞋是杏花图案,春节给馒头按上的红印是杏花图案。学生上美术课画的第一朵花是杏花图案。
杏花开时赏杏花,等杏花一落,这杏树上就结满了果子,淘气的孩子们来采食酸杏,小杏酸倒牙,连白色的杏仁都还是软的,一咬一包水。说实话,酸杏并不是很好吃,但酸杏却成为人们苦春时的味觉调剂。仿佛没有尝过它,就像没度过春天一样。
这杏树分野杏和家杏,一到了夏天,人们要到山上打野杏。野杏的杏核是村子里很好的副业,孩子秋天开学全靠着这点杏核卖钱呢。打野杏要等到生产队统一通知,杏熟了才能打,记得我们村里有一对夫妻,在山上挖了一个地窖,还没有等杏完全熟,每天半夜里上山打杏藏到地窖里,一到白天就回家,等村长通知打杏,别人刚开始打,他已经开始牵着毛驴往家里驮杏了,果然, 他两个孩子的秋季学费就够了。
村子里各家院长着家杏树,那杏我猜想是从河北玉田带来的,软甜软甜的,有点像山东的高粱饴。八奶奶的家杏黄橙橙的,每年她都用大襟袄的前襟装着送过来,妈妈就把杏儿放到红堂柜子里。虽然只在夏季放过几天时间,我家的红堂柜子里一年四季都有杏儿的香味,我们做完作业,没事儿就打开柜子闻一闻。
儿时没有买来的玩具,只有孩子自己发明的玩具。比如把杏核上下磨透,用一根钉子穿过,钉子底下砸住一个小木块,在杏核里面缠上线绳,这线绳一拉底下的木块就开始转动。孩子们管这叫核桃车,大概是当地没有核桃,就只能用杏核代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