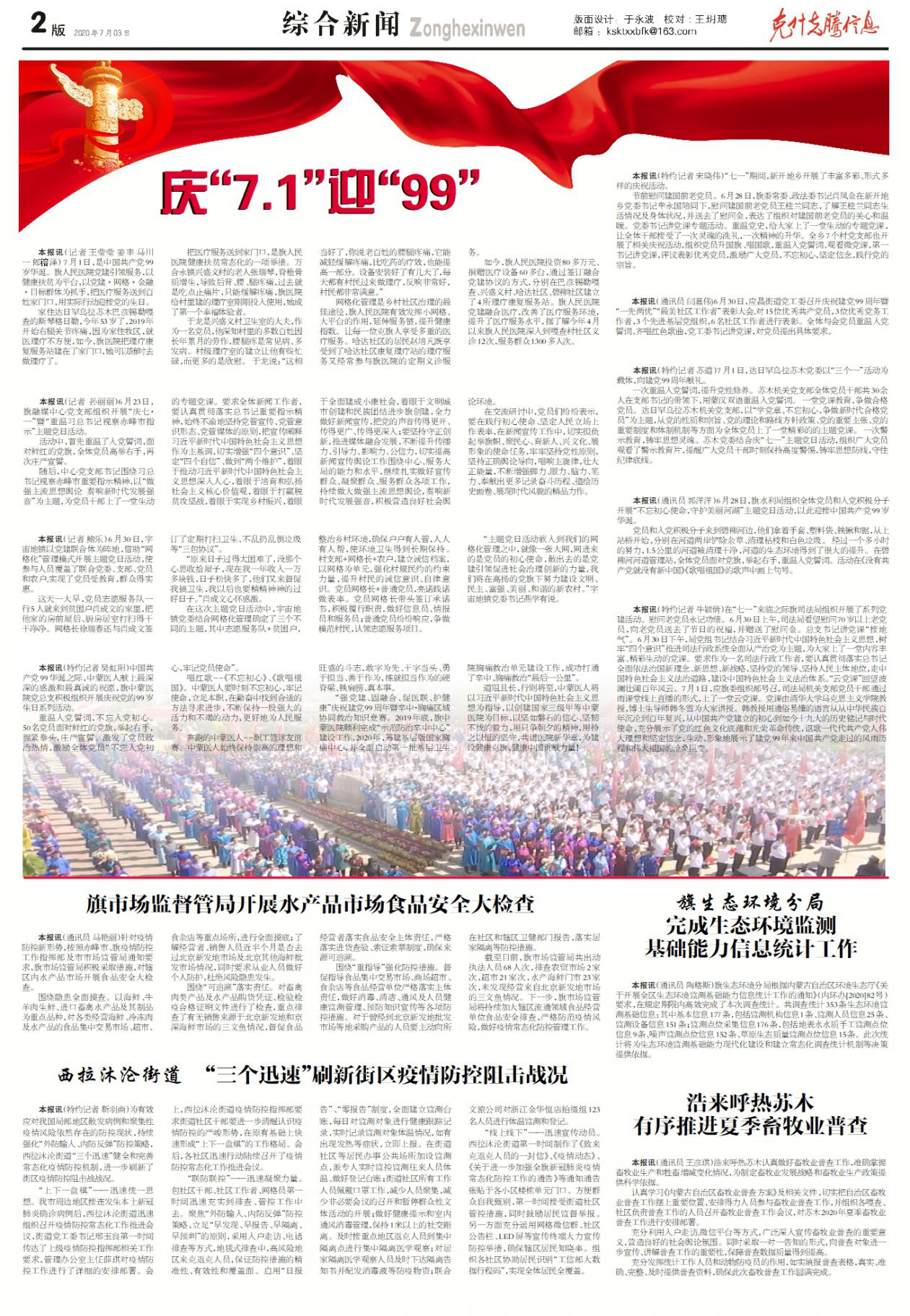第三版:3
从出生开始,在那幢老屋里,我整整生活了十三年,十三年,对于我,应该有大半的时光印象。
这幢老屋究竟是不是姥爷家的祖屋,已无从去考证,但当时隐隐约约地听年近八旬的姥爷讲,他的太爷爷也是在这老屋里出生的。如果是祖屋的话,它的屋龄应该有二百岁以上了。
老屋非常高,光是露出地面的基础石足有一米高,进出老屋须登五层台阶,台阶是用当地山里的马牙子石砌成,台阶的棱角已经磨的非常光滑,只有阶面防滑的条纹还算清晰,足见老屋年代的久远。
老屋的墙很厚,因为当时在我们那样的穷乡僻壤还没有砖瓦厂,建房造屋只能就地取材,用黄土掺和麦秸或“耙搂”之类的植物纤维和泥垛墙,但最快捷的方式是把黄土洇好后,直接用板打,这就是东北、甚至华北、西北农村非常普遍的“干打垒”,虽然“土”,但很结实,在抗震保暖方面要强于砖瓦房。
老屋的窗子也很古老,木制的的网格状窗棂,两侧各有一扇耳窗,中间还有一扇顶窗,可以自由开启,俗称“呱嗒嘴子”窗。窗子平时用草纸裱糊,只有过年时才能换一茬“昂贵”的白纸。
老屋的炕也很特别,几乎所有农村的炕都是从位于炕头的灶膛中进烟,经过炕洞后再从位于炕梢的烟道出烟。而老屋的炕是回洞子炕,即烟火从灶膛进入炕洞后,经炕梢处返回,循环至炕头底部,再从位于那里的烟道出烟。回洞子炕的好处是能够充分利用燃料的热能,使炕头炕梢温度基本保持均衡。为了保障烟火循环通畅,这种炕要比其他人家的炕高出许多,以致我五、六岁时上炕都要大人们往上㨄。
至于老屋的结构,幼年时期的的我并没太多留意,直到1976年夏末的一个凌晨,一阵剧烈的抖动伴着沉闷的轰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,姥爷惊呼“地动了!地动了!”当时对于什么是地动,我并没有一点儿概念,凭空觉得是一场灾难的降临,只是在慌乱中穿上衣服,跟着姥姥和姨姨拼命往屋外跑,当时整个村子已是鸡犬嘈杂,人声鼎沸。我们在恐惧中稍稍镇定后才发现,姥爷还没出来,回屋看时,姥爷还安然躺在被窝里,非常淡定地说:“怕啥,这房子结实,一窝纤(松木),四梁八柱,墙倒屋不塌。”
后来才知道:“四梁八柱”是我国古代民居建筑上一个传统的代名词,也是土木结构民居中最为简单实用的一种。只有三间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四根梁八根柱子,随着房子间数的增多,梁和柱子的根数也随之增加。根据人们的需求,可在“四梁八柱”的基础上改变为“三梁六柱”、“五梁十柱”、“六梁十二柱”。这样的建造技术是属非物质文化“手工艺术”类,结构严密稳固性强,有防震性,墙形变裂依然不会倒塌,成为人们祖辈传承的民宅建筑,在建筑的过程中,先搭结构、后砌墙,也叫先立木、后垒墙,上世纪八十年代后,由于森林的禁伐,混凝土代替了土木结构,无柱支撑,基本上不利用木料建筑,因此“四梁八柱”结构建筑技术将要面临失传。
从那次地震后,我才开始留意这栋老屋的建筑结构,老屋共五间,应该是典型的“六梁十二柱”。由于柱子埋在墙体里,只能从堂屋看到屋顶的结构:整个屋顶由柁(梁)、檩子(栋)、椽子,荆芭组合而成。粱和栋是支撑整个屋顶的主体,“栋梁之才”便出自于此。而椽子的作用一是均衡檩子的受力,二是拱托上面的荆芭。荆芭用柳条编成,呈席子状,上面覆上黄泥,农村俗称上芭泥,芭泥一上,便意味着一栋房屋的主体竣工。
老屋的柁、檩子、椽子都是松木的,这就是姥爷所说的“一窝纤”。大柁和二柁足有成人的一搂粗,檩子也有海碗口粗细,经年累月的烟熏潮暖,所有的房木都已变得黝黑,但没有一棵檩条或椽木变形。记得姥爷经常说,纤(松)木的的最大特点是“宁折不弯”,这是否在喻示给我做人的哲理呢?
至于这些松木来自何处,现在想象:如果当时百岔川是百里松漠,倒情有可源,但如果不是这般情形,这些松木只能出自黄岗梁林海,数百里之遥,凭二百多年前的交通运输条件,将这些庞大的木材运到这偏僻的百岔川腹地,应该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程。
为了防雨,老屋每年春末夏初都要“抹房”,就是用黄土加麦圪穰(小麦脱粒后的麦壳)和泥在屋顶抹上寸把厚。这是一项体力活,每次抹房,都要集营子里十几名壮劳力,从五更开始,热火朝天地干上大半天。为了犒劳出力的男人们,姥姥总是请来营子里几个干活麻利的妇女帮锅,蒸馒头,猪肉炖粉条,外加攒了一年的小烧,在当时艰苦的岁月,这无疑是一顿难得的饕餮大餐。
黄泥抹房可能是房屋最古老最简便的一种防雨方式,比它先进一点的就是草苫房,苫一次房能保证五年左右不漏雨,家乡的草苫房一般都是用莜麦秸或麦秸,但刷秸子的过程现在看来显然比烧砖瓦要耗时费力,况且苫房的过程也不比抹房轻松,姥爷虽然一直渴望自己的老屋有一天也能变成草苫房,但苦于家里没有劳力,直到姥姥和他相继离世,老屋的屋顶已是满坡枯黄的麦秸杆(抹房时的圪穰里有麦籽,雨水好的年景屋顶便长出麦苗)在寒风中瑟瑟地摇曳……
——老屋老了,并且失去了传人,它的“生命”也像屋主人一样将趋于终结……
我和我的姐妹都是在这老屋——西屋(东屋是姥姥姥爷居住,还有东面独立开门的两间是二姥爷居住)的老炕上诞生的,那时我们出生的条件非常简陋,母亲在临产前家人在炕头铺上细沙,把炕烧热,于是我们就出生在那温热的沙堆里。可以说,老炕,不仅是我诞生的温床,也是十几年幼年和童年成长的摇篮,从我三岁起,爸妈和姐妹们便搬出了老屋,由于对姥姥的依恋,我宁死不随同父母迁居。在姥姥身边,她把对隔辈的爱全部倾注在我身上,幼年时期,我一直和姥姥在一个被窝里,我那时非得吮吸着姥姥的干奶头子才能入睡,直到我十岁的时候,姥姥才从她那温暖的被窝里把我“撵”出来。
现在我常想:那栋老屋,曾经演绎了多少代人的恩恩爱爱、悲欢离合,二百多年的天地光阴,老屋的老炕上,曾制造、诞生并送走了多少生命……
老屋,我生命中的永恒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