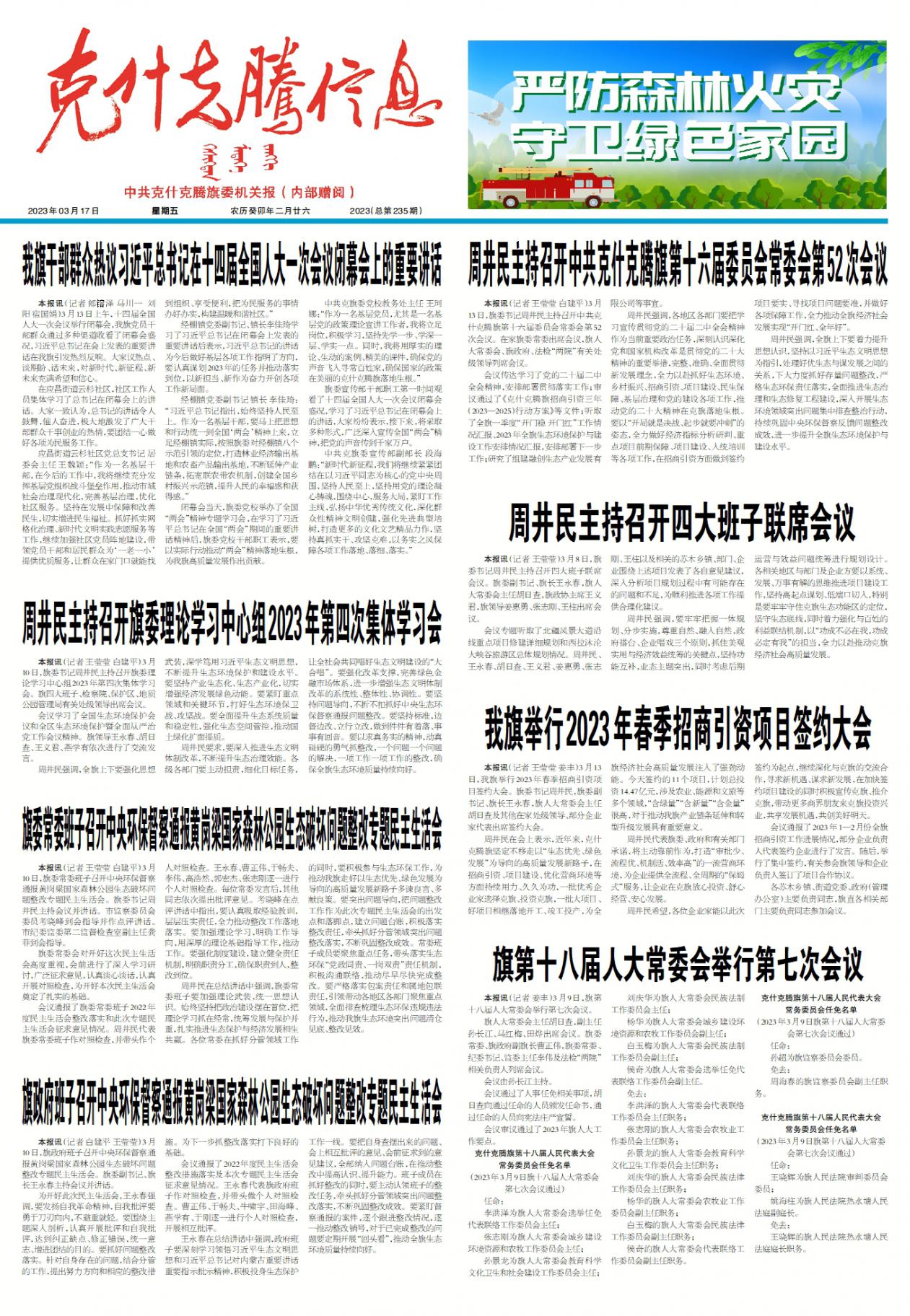第四版:4
去年腊月,我驱车一百多里回到家乡,去祭扫母亲的坟墓。这不过是寄托一份哀思,减少一点愧疚,讨得一时心安罢了。对于逝者而言,又有什么意义呢?亲戚或余悲,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,托体同山阿。母亲去世已经四年,她安眠在一个山洼里。这里背靠一脉崎岖山岭,远接原上;面对一道曲折峡谷,近通河川。山上植被茂盛,半人多高的榛柴里盖着厚厚的积雪。祭扫完毕,登上山岭高处,正午明亮的阳光下一片荒芜。荒草何茫茫,白杨亦萧萧。凄厉的山风吹过,一丛一丛白色的枯草,哗啦啦地抖动着,被风吹斜,又倔强地挺直起来!阴阳远隔,幽明异路,想起一生卑微而又要强的母亲,我不禁悲从中来,为她尽情一哭。远处有两只野鹿被我惊动,惊慌地逃走,又停下来回头好奇地看看我。它们不知人间何以会有这样的声音,稍作停留,就转过山梁,不见了。
遥望村里,一圈儿小山无言地把小村揽入臂弯,宁静而深情,老屋在那里静默着。我这次回来没有告诉父亲,也没有去他那里拿上老屋的钥匙。我知道老屋进不去了,就在村外熟悉的地方走了很久。那条山沟,这道山梁,都是我过去经常去玩耍的地方。有时候饭后去散步,放学后去读书,或者挑着筐去捡柴。如今山水依旧,人事全非!
难得回来一次,我得去老屋看看。站在门前,隔着锁闭的铁栅栏门,老屋依旧,却已满是沧桑。院里杂草丛生,蓬蒿遮路,屋门口靠墙倚着一根扁担,旁边一只水桶,几乎都被满院的荒草遮住。那是父亲一生用来挑起生活的扁担,现在他终于放下,到小城里去了。院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鸡鸣犬吠和袅袅炊烟。不到一年,老屋早已一片荒凉!这里一切都不再属于我了。我站在大门外,隔着栅栏门,凝望老屋许久,我知道自己已经被老屋流放,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,才转身黯然离去!
记得在村里读小学的时候,不管是放学后出了校门,还是假日在村外疯跑,落日余晖中,只要看见家里房顶上的袅袅炊烟,我们就会像一只归巢的鸟,飞跑回去。母亲早已做好了饭菜等着我们,喷香的小米饭,金黄的玉米饼子,土豆丝炒酸菜,还有晚上火盆里烧熟的嗤嗤冒着香气的土豆。那时候,物质生活虽然匮乏,现在想来,却是最快乐的时光吧!
十四岁那年,我上了二十几里外的中学。我在学校想家,因此而常常逃学,最终半途而废。父母恨铁不成钢,一次一次地把我送到学校,我却总是偷偷地跑回去。母亲脾气不好,一生疾病缠身,吃遍了十里八乡医生的苦药,每年两次住进医院输液,都无济于事。她的疾苦,一半源自体质,一半缘于天性。贫贱夫妻百事哀,父亲母亲常常为生活琐事争吵不休。他们希望我能有出息,从而改变家里的命运。可惜我天生是一只井底之蛙,天地之大,属于我的地方只有那口井。尽管母亲不止一次说我不长刚不长志!也没有激起我奋斗的意志。今天,我依然想着那个家!他们生我而不得济,养儿未能防老。永痛长病母,四载委沟溪,生我不得力,终身两酸嘶!
我们姐弟几个各自成家后,就都到外面谋生了,父母留守在老屋里。那时候,母亲每年都养鸡养鹅,养羊养猪。小院扫得很干净,没有一棵蒿草。平常的日子,回到家里,就会看到圈里的羊,墙根下肥胖的猪,院子里寻食的鸡。那羊粪的气味在阳光里扑鼻而来,园子里的菜应有尽有:豆角、黄瓜、大葱、韭菜,绿意葱茏。菜畦边、石墙根的扫帚梅,在阳光里开得热烈。肥胖的蜜蜂嗡嗡地飞着,蝴蝶伏在花蕊上。母亲在锅台边忙碌着,父亲劈柴烧火,房顶上那个早已熏黑的烟囱里,升起袅袅的炊烟。那熟悉的烟火气,就把我带回童年的岁月。
腊月里杀猪的时候,我们几个拖家带口,浩浩荡荡地回去吃猪肉。吃完了要走的时候,母亲还要再给我们带上一些。母亲一生很少走出这里,这一圈儿乱石围成的破烂不堪的院落儿,三间土屋,半亩菜园,连同那几只鸡,几头猪,就是母亲的整个世界。
后来母亲身体更加不好了,她已经不能走路,每天只能坐在炕上,生活基本不能自理。我们再回到家里,来到大门口,院子里那两只鹅总会嘎嘎地叫着,把我们当做陌生人。在大门外就能看到玻璃窗里坐在炕上的母亲,从窗口望着我们。母亲不能走路已经好几年,每天就在那里坐着,她似乎一直在那里等待着我们。当我们推开大门走进院里,父亲就会迈着蹒跚的脚步,打开屋门,大声地驱赶那两只张开翅膀、伸着脖子要来啄我的鹅,还有那只拴在铁链上狂吠的狗,直到我们心惊胆战地走进屋里。
斯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尽乡愁。母亲去世后,父亲自己守着老屋住了三年。空荡荡的老屋里,只有他一人守望。但是他的小园子里依然种满了水灵灵的蔬菜,虽然他腿脚不便,在他的精心侍弄下,一畦畦绿油油的菜长势旺盛。秋天收获的时候,院子里高高的木杆上,就挂着一串串通红的辣椒,一辫辫饱满的大蒜,蔚为壮观。其实他自己吃不了多少,年迈的他已经没有别的什么了,他是想把那个小院作为我们后方的蔬菜供应基地。他知道,城里的菜那么贵,冬天里的一棵葱或者一头蒜,也得一两块钱。
去年,父亲走路更加艰难,春天时他还是种上了菜。夏天,我们把他安置到了小城里,轮流去照顾他。他托付邻居照看他的老屋,干旱的时候给他浇浇园子。有一天,他坐班车回去看他的菜园子,在家住了几天,回来的时候,又带回了大袋小袋的蔬菜。我看到他分好了摆在地板上,要分给大家。但是,不理解父亲的我,拒绝了他给我的那一份,因为我自己在乡下也有一个菜园,这些年我都是自己种菜,自给自足,多余的还要送给亲友一点,有时候还给他带一点辣椒黄瓜什么的。因为我不要他的,后来他就不再准备给我的那一份了。
胡马依北风,越鸟巢南枝。父亲来到小城后,在他床头的墙上,挂着一串用红丝绳拴住的钥匙。那是他住了一辈子的老屋的钥匙,在他的心里,这里只是暂住的寓所,永远不是他的家。他的家是乡下的那几间老屋,他把钥匙带在身边,挂在床头,就如同老屋在他身边。
如今,那白铁栅栏的大门,只有一把冰冷的铁锁守护着。院子里静悄悄的,什么也没有了。屋中墙上挂着的镜框里,一张张老照片,沉淀着远去的岁月!记录着我成长的足印。照片里,母亲坐在板凳上看着我们,目光温柔而深情,是在为我挂牵,还是为我祈福?照片外,我无言地看着照片里的母亲,无限感慨,泪流满面!老屋里清锅冷灶,到处灰尘,每一件他们用过的东西,都让我触目伤怀!没有父母的故土,我只是匆匆过客罢了!几间老屋里,尘封了多少恍然如梦的往事,和那一个又一个烟火红尘的日子。
故乡飘已远,往意浩无边。再也不见老屋那窗户上昏黄的灯光,那扇曾经随时可以为我打开的门。这曾经生我养我的土地,一草一木都不再属于我!数载恍如隔世,咫尺已是天涯!
岁岁秋霜惊雁阵,悠悠南下几度回。
又是惊蛰春气暖,匆匆一字向北飞。
惊蛰到了,大雁也早已在北归的路上日夜兼程了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