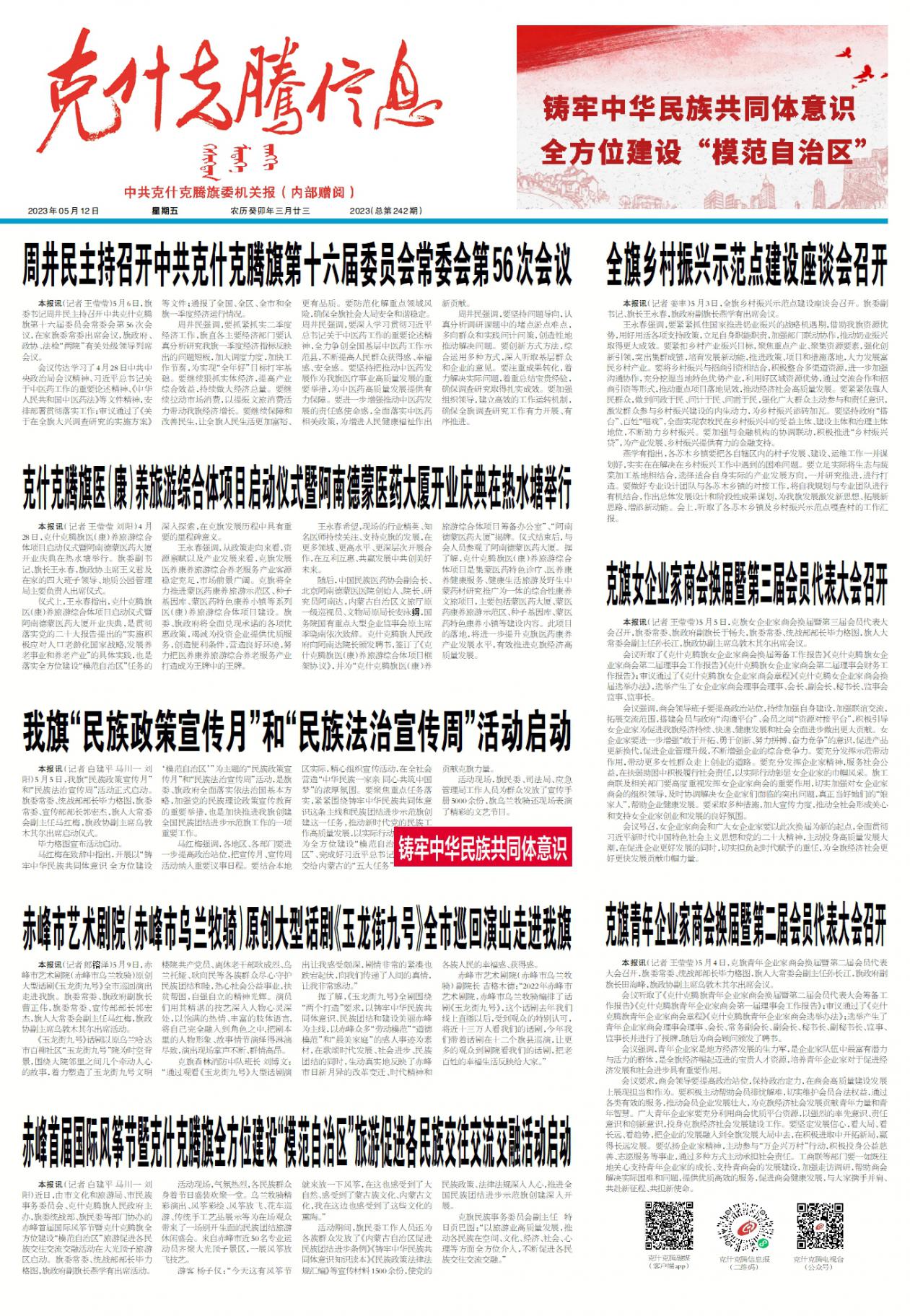第三版:3
大鸨是鹤形目鸨科的大型地栖鸟类。栖息于广阔草原、半荒漠地带及农田草地,通常成群一起活动,十分善于奔跑。大鸨既吃野草,又吃甲虫、蝗虫、毛虫等。主要分布于蒙古、俄罗斯、中国和朝鲜半岛。据不完全统计,全世界现存二千余只,属于濒危物种,其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。近些年更为少见,我已经三年没拍到大鸨了。
大鸨在贡格尔草原是候鸟。初春季节到来,初冬季节去山东、河北等地越冬。在我国大鸨俗名“地捕”,它要比大天鹅的体型还要稍大一些。大鸨在贡格尔草原的主要栖息地在达里诺尔保护区,零星散居在白音敖包、浩来呼热、乌兰布统、巴彦查干等地。2019年以前,我们的拍摄基地主要在达来诺日镇周边。那时候那里还是一片草原,栖息着很多珍奇的鸟类和哺乳动物。春天在这片湿地里可以看到成群的大鸨、白枕鹤、蓑羽鹤、天鹅、鸿雁、赤麻鸭、绿头鸭等。冬春季节这里是野生狍子的乐园,也偶见狐狸游走其间。这里是一个动物的天堂,我的很多摄影作品都出自这里,后来这里由于开垦成了田地,动物们很少见了。其它草原上布满了网围栏,只能远观,拍摄也就成了奢求,就这样我的800定焦“大炮”闲置起来。由于没有“好鸟”可拍,曾经一度产生了卖掉拍摄设备的想法。
四月中旬,几个摄友去拍斗鸡。斗鸡学名黑琴鸡,每当初春为了争夺交配权,几只雄性就会争斗月余,最后分出胜负。胜者领着一群母鸡,败者只能灰溜溜的溜走。在争斗期间几乎不怕人,车能开到跟前,有时候斗的激烈能一直打斗到你的眼前。于是又抄起家伙,磨炼一下快要生锈的“大炮”。
在拍摄斗鸡回家的路上发现这批大鸨纯属偶然,因为在我们的记忆里,在这片开阔的草原上从没有发现过大鸨的踪迹。摄友老张说:“慢点开,看看能不能发现好鸟”。我说:“这个区域还从来没见过好鸟呢,偶尔有几只蓑羽鹤,也是距离很远,没啥意思”。话音刚落,老张喊“停停停”。我一个急刹车,慢慢靠向路边停稳车,在右侧的草原里距离我们200米以外的地方,那分明就是我们找了好几年的大鸨!激动地心快要蹦到了嗓子眼,匆忙开始拍摄,回放、放大,不太清晰,此时太阳已高,在太阳的照射下,草原上水汽蒸腾起来形成了扰流,很难拍摄,非常扫兴。大鸨就在眼前悠闲地觅食、踱步,我们只好望鸟兴叹,只能观赏。在平时就是观赏也是奢求啊!
大鸨有个习性,它们的活动的区域相对固定。今天在这里发现它们,这里就是它们的领地,如果不受到大的惊扰,它们不会轻易转场。于是和老张商议,明早起早来。
就这样我们开始了精彩的大鸨拍摄之旅。
在大鸨栖息的这片草原,是牧民的夏牧场,通常每年六月初牧民们才赶着大群的牛羊前来驻扎放牧。在这个时节草原上静悄悄的,为大鸨的生活觅食提供了一块暂时的净土。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对这群大鸨的影响,老张我俩决定“吃独食”。首先,拍鸟最好一车两人,前后排靠左侧,不用下车,人一下车活动鸟就会飞走。把“大炮”架在车窗上拍摄,两台车以上就会惊扰鸟类,不利于拍摄;另外,很多拍摄鸟类的影友通常有一个不好的毛病,总是想靠近、靠近、再靠近。然后为了一张精彩的飞板,要闹出动静,甚至下车哄撵,有的甚至出动无人机,经过惊吓的鸟通常就会转移阵地,以后再想拍就找不到了。这些正是我们深恶痛绝的。
初春乍暖还寒的草原还是比较清冷,大鸨们正在草原上觅食,大鸨觅食的时候头后部向上抬起,嘴尖向下,两眼注视地面,不时地转动头部,观察地面的昆虫、其它小动物和植物种子等。吃草时常常先用嘴将草咬住,颈向后缩,再用力抬头,将草拔断,然后吞下。有时伴随着两脚向前用力蹬地,身体向后退,双翅微展或半展。春天的草原上还没有昆虫和小动物,他们只能吃一些植物散落在地的细小种子和枯黄的草叶。
大鸨无疑是草原上最美丽优雅的鸟。美丽的褐黄色花纹衬着黑色的斑纹,腹部灰白色的羽毛,远距离看像一叶扁舟在草原上游走,细长的脖子有时高高抬起,警惕地逡巡。
这是十几只雌鸟,大鸨在繁殖季雌雄分群,雄鸟通常不会距离太远。为了尽可能地不惊扰它们,我们把车停泊在距离大鸨200米以外的地方静静地观察、拍摄。第一天我们始终和大鸨保持安全距离,不过多的打扰它们,让它们感觉不到威胁,逐渐熟悉我们的车。
草原上的天气变化多端,第二天下了一层中雪。草原上刮起了风,碎雪伴随着风,在草原上形成了一层雪雾。我们还没有拍摄过雪中大鸨,在途中很是兴奋。赶到大鸨栖息地太阳还没有升起,借着雪地的映射草原上已经很亮了。我们开始寻找,始终找不到大鸨的影子。失望之余,只能徐缓地沿着车辙向草原深处挺进。太阳升起来后,我们一无所获,正准备打道回府,转过一道小山梁就隐约看见,在我们来时的路边有很多小黑点。用“大炮”拍一张放大,这就是我们寻找的大鸨啊!我们来时没看见,肯定是一阵白毛风遮住了它们的身影。
驱车小心靠近,大鸨们静静地趴卧在雪地上,一动不动。偶尔有几只站起来觅食,但是很快又趴卧下来。草原上已经被大雪覆盖,它们也很难觅食了,只能趴卧下来节省体力。雪天的大鸨很不活跃,我们静悄悄地拍摄了一会儿,也没有惊扰它们。好在气温马上升高,草原上的雪到中午就会融化。
太阳还没有露头,天气晴好,湛蓝的天空,一丝丝薄云,没有风。我们目力所及已经发现了两群大鸨。我们不约而同的说:“来菜了”。
其中一群有七只大鸨,远看白白的,那一定是雄性翻卷着的生殖羽。大鸨每年四月中旬开始繁殖,和斗鸡(黑琴鸡)争夺配偶权有些相似,斗鸡是翻起羽毛,特别是尾羽,开始打斗。大鸨是翻转全身的羽毛炫耀,喉部因急速不断的吐咽动作和呼气而膨胀成悬垂的气囊,颈下裸露的皮肤变为蓝灰色,被竖起的颈下须状羽分为左、右两条。然后将头向后仰缩向背部,颈下须状羽竖起直至胸前,尾羽向背上平展呈扇状,几乎触及头部,双翅向体后下方伸展,大而白的覆羽向上翻转而呈扇状。同时双脚有力地走动,互相撞胸,有时围绕着另一只雄性大鸨转圈。不鸣叫,只是发出呼气的斯斯声。偶尔原地接连着跳跃,它们是用这种方法展露自己的雄性体魄,让同类有畏惧感,谁最雄壮才会有优先交配权。它们在表演期间警惕性不高,我们得以逐渐靠近,果然不出所望,拍到了赏心悦目的大鸨繁殖羽照片。
就这样,我们连续拍摄了十多天,每天都有精彩。大鸨们熟悉了我们的车,可以靠的很近。在自然状态下,它们起飞、降落、觅食、踱步、展露漂亮的羽毛……
知足常乐,我们决定今年到此为止。可是隐约有些担心,六月初牧民们要出夏场,这里有十多处牧民出场的蒙古包痕迹,到时候这里一定是遍地牛羊。大鸨们的生存空间会进一步压缩,它们该何去何从?我们更担心,它们一旦把蛋产到这片草原上,有可能会前功尽弃!

摄影 八路